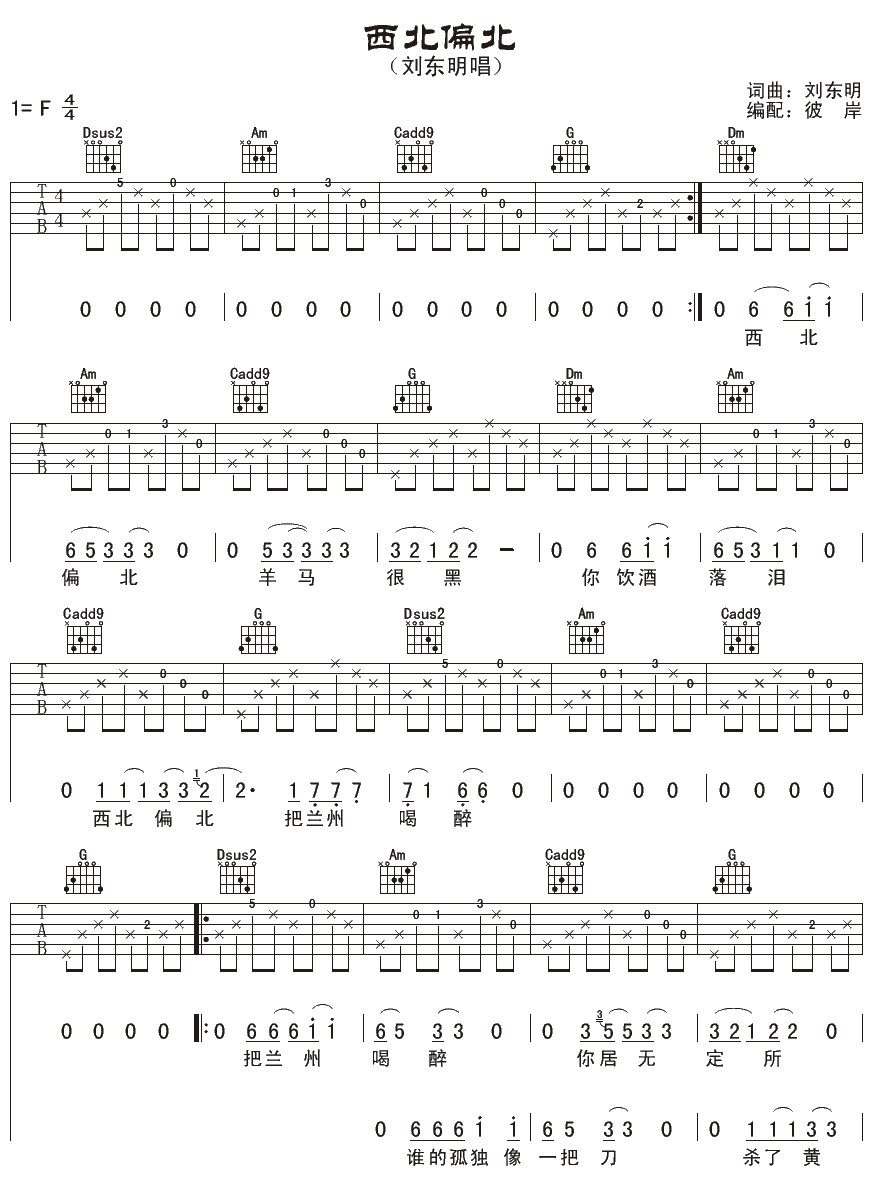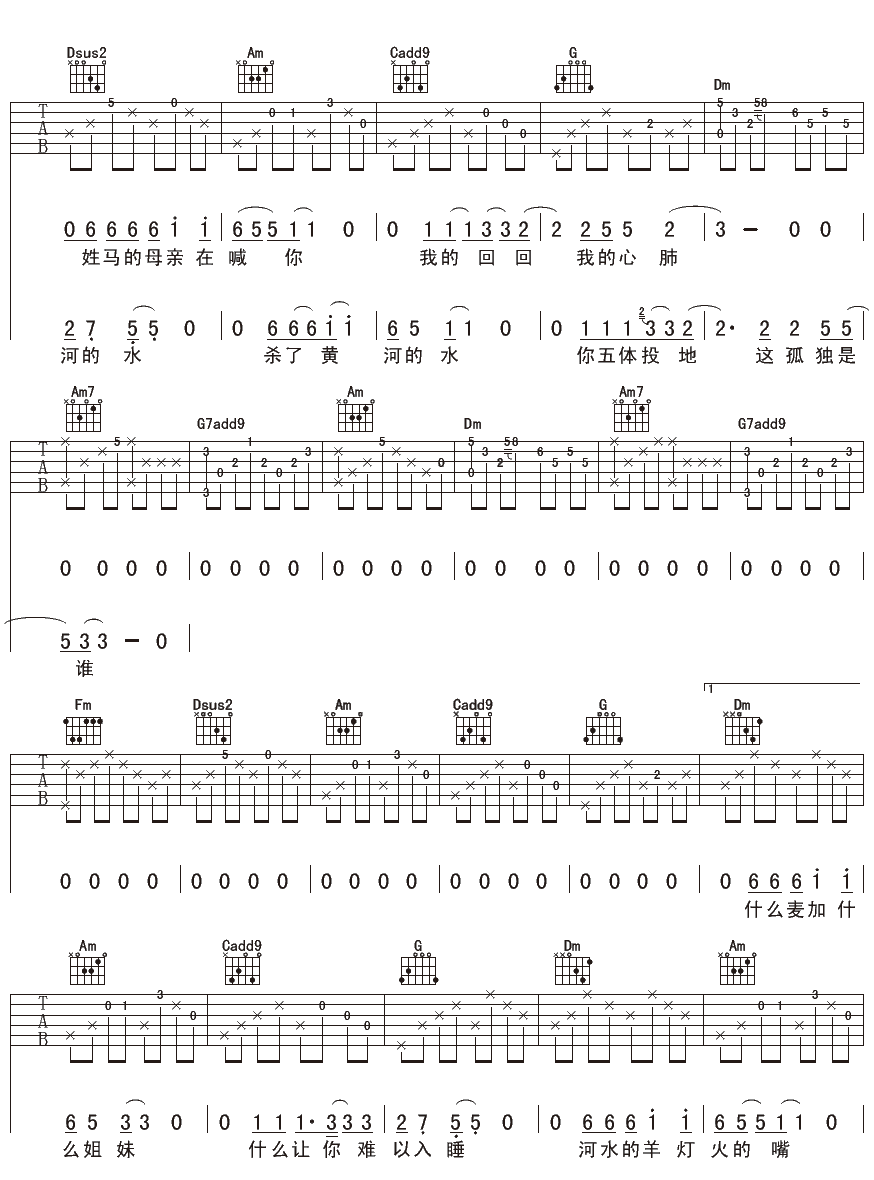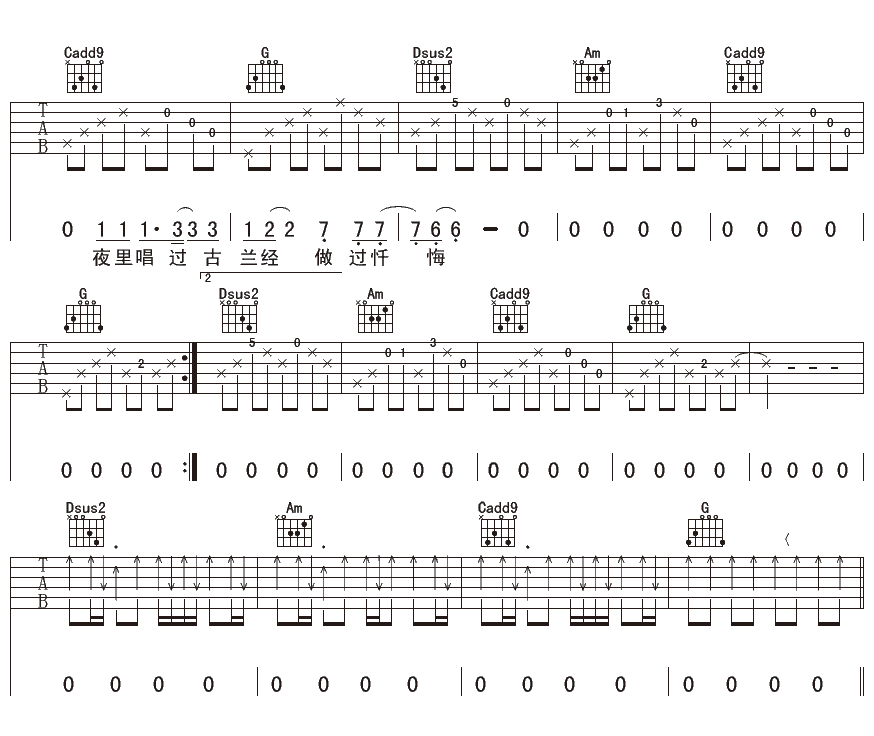《西北偏北》以地理方位为隐喻载体,通过荒凉旷远的意象群构建出精神漂泊的图景。歌词中“风沙卷走地名”的苍茫笔触,既是对地理坐标的消解,也是对现代人身份认同困境的诗意呈现。锈蚀的站牌与废弃的钢轨构成工业文明褪色后的残影,在“黄沙埋住车灯”的意象中,物质符号最终被自然力量重新回收,暗示着所有人为标记在时间维度里的临时性。羊群啃食落日的情景将生态循环与时间流逝并置,血红晚霞成为生命燃烧最后的视觉残像,而“鹰在经幡上盘旋”的垂直构图,则赋予荒原以宗教性的凝视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方向词构成矛盾的张力,西北偏北这个偏离正方位的地理概念,实则指向当代人精神坐标的模糊状态——既非彻底的迷失,也非确定的归属。所有跋涉痕迹终将被风化的结局,解构了传统漂泊叙事中“寻找意义”的预设,转而呈现生命本身在荒芜中的原始质地。这种对存在本质的袒露,使歌词超越了地域描写的表层,成为现代人精神荒原的象征性书写。